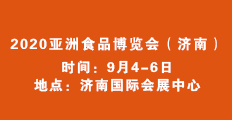黑衣、黑裤、黑框眼镜、黑胡子,刘伟民的标志性装扮透着文艺范儿。每当我向朋友介绍这位帅气的男士时,无人不惊叹于他的多元身份:大中华酒评人协会会长,五本畅销葡萄酒书籍的作者,葡萄酒讲师,国际酒展评审,专栏作家。“这么年轻,你曾经是童工吗?”这是最常听到的赞叹。
让人惊叹的不只是他的童颜,还有他神奇的从业经历。最不喜欢写文章,却执笔二十年;最头痛做生意,却创办了香港第一所楼上音乐会所与两本独立音乐杂志;最难接受批评,却成为随时被人点评的酿酒人;最讨厌教学,却桃李处处,常被人以“刘老师”相称。
然而,他更喜欢把自己称为爱喝酒的乐评人,爱音乐的酒评人。因为他的人生里,一半是酒,一半是音乐。
从针笔到圆珠笔
“我最讨厌写文章。” 曾经为近一百份报章杂志撰写专栏、经营过两本独立音乐杂志、著有五本畅销葡萄酒书的刘伟民,居然在采访的开头抛出这样一句话。
“我上学的时候学的是设计课程,本来天性懒惰不想找工作,在母亲的逼迫下去了全球第一本中文饮食杂志——《饮食世界》,但我不是做编辑,而是做平面设计。”80年代没有电脑,日复一日的手工粘贴、剪切、排版,让刘伟民倍感沉闷,“当时杂志的负责人是香港的第一代食家梁黛玲小姐,她看到我对本职工作兴味索然,就让我尝试写文章。我从来害怕写作,也不看书,一直觉得自己只能拿针笔的,怎么可能拿圆珠笔呢?但是她坚持让我尝试,于是我做了第一篇关于金钱龟与癌症的文章。”
“虽然说我只是把它当作一项额外的任务来完成,但是为了文章尽量客观,我还是用了两周的时间来做调研,并且三番四次修改后才交稿。梁小姐对结果很满意,逐渐向我每月约稿,并且让我跟着她四处参加社交活动,试吃试饮,结识酒商和厨师等,我也最终转型为饮食编辑。”
无心插柳,这杆圆珠笔一拿就是五年半,刘伟民积累了经验和人脉,直到饮食杂志竞争愈见激烈。“70年代香港平面媒体的饮食栏目都是经济记者或者体育记者兼任,直到80年代开始才出现专门的饮食记者。当越来越多人注重饮食,杂志的竞争也愈来愈激烈。在前景初现阴霾时,机会也同时出现。“过去没有电邮,只能亲身跑到各个出版社送文稿和图片,如果只送一篇稿件,时间和金钱都很划不来,于是编辑们让我‘顺便’也写写音乐。”
爱喝酒的乐评人
就这样好不容易奠定了写食评酒评的基础,刘伟民转型成了乐评人。幸而音乐和酒一样,是刘伟民从小就培养起来的兴趣,“在其他小朋友嚷着让家长买糖的年代,我已经拉着父亲的去买黑胶唱片了。”
80年代是唱片业最蓬勃的时候,但是香港的唱片店环境很差,没有地方享受音乐,只有拥挤的环境,顾客无法投入音乐,也无法忠诚地支持唱片业。刘伟民于是在1992年创办Music Union(音乐联盟),是全港第一家有现场乐队表演的音乐会所,有会员制度,甚至有会刊《New Generation》,后来发展成正儿八经的音乐杂志。
“店铺在尖沙咀旺区的二楼,有舒服的沙发可以试听唱片,有认真冲泡的意大利咖啡,有好的歌手和乐队现场表演,唐朝、黑豹、Beyond,Radiohead、王菲、关淑怡、林忆莲,都来表演过。还附有时装精品店,卖与音乐有关的时装品牌,都是我自己从世界各地搜罗回来的,从散卖到品牌代理,例如德国拖鞋品牌Birkenstock,当时也是我带进香港的。”这在当时的香港该是多么创新的经营模式啊,即使今天看来仍在潮流尖端,本应大展鸿图,然而事与愿违。“当时没有人能接受楼上铺,也没有品着好咖啡休闲听歌的氛围,所以只坚持了四年半便结束了。当时还在做电台DJ的香港作曲家陈辉阳也是我的会员之一,他为此帮我做了一个马拉松式的告别音乐会,邀请达明一派、林忆莲、关淑怡等红星来现场演出,从下午唱到晚上,持续十几小时,并且在商台直播。我的会员伤心流泪,我反而觉得是一种解脱,因为做生意太辛苦了。”
当唱片公司开始财政主导,不再愿意用钱与资源堆砌一个音乐梦时,香港的唱片业开始萎缩。对唱片公司工作开始倦怠的刘伟民嗅到了慢食运动与葡萄酒的气息。“意大利兴起了慢食运动的时候,我想开创一本以此为主题的饮食杂志,但是所有的朋友都不看好。我不再犯想法太超前的错误,因此回归音乐,创刊《Jam》,发展多媒体音乐文章来源于中国红酒网杂志,每期附上VCD,依靠唱片公司的关系,放进国内外流行的音乐录像,还有我自己帮香港独立乐队制作的音乐电视。直到2003年SARS爆发,杂志才停刊。”
爱音乐的酒评人
岁月荏苒,辗转做了十年的乐评人,刘伟民始终割不断与酒的联系。
“我一直喜欢意大利酒,本来想带着太太到酒庄旅游,然而发现独立联系非常困难,不是不会英语,就是不接待私人。机缘巧合,《明报周刊》向我抛出橄榄枝,提供我一个去皮埃蒙特(Piemonte)拜访酒庄的机会,条件是我要开始‘三百杯’的酒评专栏。自此再踏入‘火坑’,又开始了为各种报章杂志写专栏的日子。”
十年人事几番新,酒圈尤是。刘伟民从旧人变新人,又花费了一番时间和努力重新积累人脉和资源。“做事如果不能投入,就一定不能长期,那不是我所希望的。既然答应了,就要做到最好。”因此那两个礼拜的皮埃蒙特之旅,他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来整理图片和笔记,让“三百杯”变成了酒友粉丝的专栏,吸引了香港和国内的其他媒体纷纷向他邀稿,其中也包括我。
从乐评人再次变身酒评人,这转变辛苦吗?“写酒评和写乐评并没有根本的区别,都是要先了解创作哲学,然后评判作品是否能融入时代,如果作品很好但是脱离现实了,也不能算是成功的创作。这是我看世界的方式,很简单。我过去失败的经验,就是因为时机把握得不对。”他还不忘自嘲一句。
刘伟民讨厌写作,其实是因为他了解自己完美主义的个性,如果不能做到最好,他宁愿不答应,不交稿。无论稿费高低,他所付出的汗水是一致的。读他的文字能感受到他的使命感,一个媒体人的使命感,“那么有趣的葡萄品种,那么好的酒,为什么我们不让更多的人知道呢?”至今,他已经出版了《倾倒葡萄酒》、《世味葡萄园》、《酒为上著》、《说葡萄酒的语言(法国篇)》和《世界知醉》五本葡萄酒书籍,他希望能保持每年至少出一本书的频率。
计划之外的酿酒人
现在,命运又让他做了一件似乎超前于潮流的事情,成为一个酿酒师。
“我通过意大利翁布里亚(Umbria)的酿酒师朋友认识了意大利名庄福地酒庄(Feudi di San Gregorio)的前首席酿酒师马里奥·艾可里诺(Mario Ercolino)。一次午餐时我谈起我在加州纳帕谷(Napa Valley)一个酿酒比赛中夺冠的经历,促成了我和他共同打造‘Dolce Vita’这个精选酒品牌的合作。成为酿酒人从来不是我的目标或者规划之一,要知道,做酒评人要简单得多,爱夸就夸,爱损就损,变成酿酒师,就面临着其他酒评人对自己的酒的批评,我可不是很能接受批评的人。”刘伟民笑说。
马里奥在意大利是一个伟大的人物,他将南部产区坎布里亚(Campania)的酒带进所有的免税商店,让一个本来默默无闻的产区蜚声海外。刘伟民首先与他合作了一款超级托斯卡纳(Super Toscana),50%桑娇维赛(Sangiovese)、25%赤霞珠(Cabernet Sauvignon)和25%美乐(Merlot)的混酿。“我没有参与葡萄采摘,但是参与了桶边试饮(barrel tasting),挑选不同的木桶,以及不同的混酿比例。尽管现在的比例我理想的风味,但是起码是整数,容易控制,要知道我并不能常驻在当地实时监控。”
“Dolce Vita”是一个跨产区概念的品牌,借马里奥在不同产区担任酿酒顾问之便,刘伟民会与他一起挑选适合中国人口味的酒款,将它们都装进这个品牌下,这在意大利又是一个新概念。“我会挑选口感平衡、易开易饮的酒款,不需要搭配任何东西就很好喝,也不需要长时间的成熟。因为懂酒的人自然会去挑选自己喜欢的酒庄,入门者则需要选购方便和保证品质。”
首次推出的酒款中只有他手上拿着的超级托斯卡纳有名字——“Aristel”,是拉丁文“最好”的意思,酒标上有音符标记,仿佛暗示着酿酒者与音乐紧密联系的。“我也负责设计酒标,这是我第一次设计酒标,我还不满意这个结果,要考虑中国消费者的喜好,也要考虑贴在酒瓶上的效果。马里奥提议我做一个颈标,写上‘Ronny Lau Collection’。”
目前刘伟民的酒还没有正式推出市场,但是我相信,他的酒也会像他一样,洒脱,多元,让人意想不到。